近年來,越來越多高中生和大學生主動籌辦社課、營隊與跨校活動,這是一種值得鼓勵的現象,展現了他們對學習的熱情與自我實踐的渴望。
但在這波「學生主導教育活動」的風潮中,我們也開始聽到一些聲音,認為:「老師其實沒這麼必要,學生自己也能教、能設計課程、甚至能經營社群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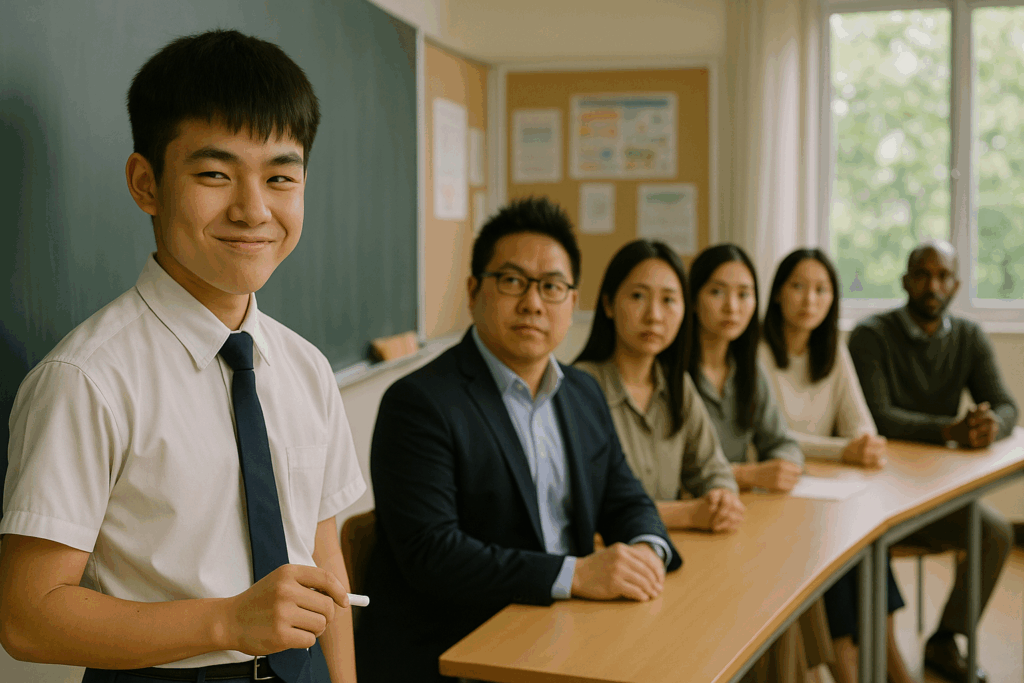
這樣的觀點,乍看之下合理,實則危險。因為它模糊了「熱情參與」與「教育專業」之間的根本差異。
更現實的是,當這些活動成功時,它們成為高中生學習歷程檔案中的亮點,甚至讓人覺得『我們也可以很厲害』,為將來進入某些大學、甚至未來從事類似教育工作的想像加分;
但當活動失敗、教學品質不足時,真正承擔後果的從來不是他們,而是第一線的體制內老師,或是長期經營教育工作的專職講師們。
大學生更不需負責,因為他們隨時可以回歸原本科系,毫無後續責任壓力,也沒有任何制度或道德機制約束他們、迫使他們負起應有的責任。
作為一位長期在教育現場帶領學生與助教的教學者,我必須誠實指出:學生的短期教學經驗,無法取代一位真正老師所經歷的養成過程。
就算他們寫出了一份看起來很完整的計劃書,如果不是以教育為全職工作,缺乏長期實踐與回饋的循環,那到底又能做出什麼來?
能打英辯,不等於能教課;能教課,也不等於能做一個稱職的教練(coach)。
教育現場從來不是「講得頭頭是道」的人勝出,而是「撐得久、看得細、扛得住」的人留下。
我們怎麼看待助教制度?
在我們的實務經驗中,助教從來不是一種「榮譽頭銜」,而是需要經過觀察、協助、實作與反思循環的學習歷程。
我們傾向建立一種階段式的培養架構,讓助教在明確的責任區塊中逐步熟悉教材邏輯、現場互動與學習者的狀態。
這不是要把學生推到第一線,而是讓有志參與教學的人,能從旁觀察、支持,到最後有機會「在專業陪伴下」進行片段實踐。
這樣的制度設計,不是為了取代老師的角色,也不是假裝他們可以勝任整體教學,而是為了讓他們理解:即使經過了討論與規劃,也無法跳過真正的現場經驗與責任承擔。
台灣許多高中社團之所以被標榜為學生自主,往往只是因為學校資源不足、制度放手,讓學生誤以為自己已經可以獨當一面。
我們反對那種制度設計只是讓學生熟記職稱、流程,卻完全不需對學習成果負責的形式參與。
助教的歷程不是「當了一場主持人」或「排完一次課表」就算數,而是要經歷教學責任、現場修復與自我修正的實務挑戰。
如果只讓學生模擬權力結構卻不讓他們體會後果與修正機制,那只是在複製空殼幹部,不是在培育教育助理。
專業老師的養成,需要什麼?
不論是在體制內的國中、小學、高中職教師,或是在體制外從事教育工作者,他們都需經過以下訓練與歷程:
- 學科知能與教學設計能力:不只是「會一科」,而是知道如何設計出能促進理解、評量有效的課程結構。
- 教育理念與專業倫理:不只是喜歡分享,而是理解「為何而教」、「對誰負責」、「怎麼處理學生失誤或衝突」。
- 班級經營與輔導能力:能應對不同學生的情緒、學習歷程,包含如何處理失衡、霸凌、或壓力問題。
- 持續反思與進修能力:真正的老師永遠在更新教法,接受回饋,不是交一份教材就結束責任。
而這些能力,不是做幾次社課、跑幾場營隊就能擁有的。
那學生能做到什麼?哪些不能?
學生當然可以學會設計有趣的活動、編排議程、甚至創造很棒的社群參與氛圍。
但他們的角色與限制也必須被誠實說清楚:
| 面向 | 專業老師 | 學生主導活動 |
|---|---|---|
| 教學設計 | 系統性、可評估、階段設計 | 主題式、片段式、短期熱忱 |
| 學生輔導 | 具備處理學生情緒 與學習困難經驗 | 通常無法進行系統輔導 |
| 教育責任 | 需回應學習成果、 家長期待、教學風險 | 無法律與制度責任 |
| 成長方式 | 理論訓練+現場實踐+專業協助 | 多為經驗學習與同儕回饋 |
簡單來說,學生活動有價值,但無法承擔教育專業的角色責任。
為什麼我們仍需要「老師」?
教育不是把教材生出來就結束,更不是幾小時規劃或演練後就能上場。
真正的教學,需要時間累積、現場經驗、不斷修正與長期陪伴,這是一種專業,也是一種對學生學習成果負責到底的投入與承擔。
當一個學生說:「我們也可以教」時,我想問的是:
- 你能面對學生的自我懷疑嗎?
- 你能因材施教、長期陪伴某個狀況不佳的孩子嗎?
- 當社課結束後,你願意為他的學習負起什麼責任?
這不是否定學生的能力,而是提醒整個教育社群:不要把熱情當專業,也不要讓模仿取代引導。
真正的教育,不會從「讓老師退場」開始,而是從「老師與學生攜手成長」開始。
他們怎麼說:我們聽過的話
有些家長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們:
「現在的孩子做個社團就覺得自己可以教人,我不是不給他們舞台,但最後學壞、學歪、沒學會的,是我們家長跟學校老師在幫他們收拾。」
某位第一線老師曾私下這樣說:
「我們不是怕學生做事,是怕他們做錯事卻不用負責。那些活動的光環、履歷、學習歷程,都跟我們無關,但爛攤子永遠落到我們頭上。」
另一位熟悉教育政策的學者也指出:
「很多助教制度說是培力,其實只是裝飾用的頭銜堆疊。如果沒有清楚的責任界線與實務歷程,那根本不叫參與,只是在練習逃避教育的真實壓力。」
延伸閱讀與資料參考:
- 教育部《師資職前培育政策實踐》:https://www.teach4taiwan.org/一個教師的誕生-師資職前培育政策實踐/
- 教師專業評鑑網站:https://tl-assessment.edu.tw
- 天下雜誌〈教師該培養什麼能力?〉:https://www.cw.com.tw/article/5116969
- 朝陽科技大學碩士論文《教師專業成長研究報告》:https://ir.lib.cyut.edu.tw/bitstream/310901800/22825/1/5.pdf
- ATER 教育研究期刊第12卷《體制內外教育專業養成比較分析》:http://www.ater.org.tw/journal/article/12-8/topic/10.pdf
